泰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启示

泰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诸多启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着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在城市存在着较发达的现代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一个较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享有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却存在一个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人数众多、比较贫穷的农民大众。这样一种状况就形成了二元社会,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二元社会很容易形成矛盾对立,对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威胁。

泰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诸多启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着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在城市存在着较发达的现代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一个较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享有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却存在一个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人数众多、比较贫穷的农民大众。这样一种状况就形成了二元社会,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二元社会很容易形成矛盾对立,对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威胁。
泰国是个农业国,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60%-70%的人口仍住在农村。1960年代前,泰国的城市内部除了对自然资源产品的粗加工外,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制造业,经过战后的恢复时期,泰国于1954年制定了“工业投资鼓励条例”。1960年代中后期,泰国的经济结构开始明显转变。
纵观1960年代后期泰国的整个城市化过程,是在一种“畸形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下进行的,即城市化过程缺乏农业发展的基础。城市人口的扩张并非是由农业现代化催生出的城市机械人口的增加而造成的,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的“拉力”而非农村的“推力”造成的。农村内部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以及政府将大量的工业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城市地区,也进一步限制了农村的发展,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批城市失业工人返回农村,也进一步加重了农业的负担,泰国城乡人口贫困差异依然明显。
伴随着泰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然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泰国6000万人口中只有50万人接受过中等教育,学龄前失学儿童91%集中在农村,教育体制的落后以及人力资本地区性分配不均使得泰国工业化进程不得不面临人力资本的匮乏问题。事实上,196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在制定第一个经济发展长期计划时就十分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70年代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年增长率为34.5%,1990年教育经费已经占到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19.2%。但是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首先,泰国多数中学都分布在城镇,农民孩子去城镇读书,课余时间就不能帮助家庭进行生产活动,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因而增加了农户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其次,泰国农村非集约化的生产技术状况使得学生毕业后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学到的知识很难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从而增加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风险。在有限的农业收入制约下,许多农户不得不放弃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资。
泰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启示
泰国的城乡经济鸿沟和贫富差距是历史形成的,但是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这种鸿沟和差距就会逐步缩小。然而,以往的泰国政府并没有真正关注过农村的发展。客观地说,他信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认真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总理。他信政府先后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允许农民推迟还债三年,给每村100万铢贷款作为发展基金,实施“一乡一产品”种植,“30铢治百病”等政策。在2001—2005年他信当政的5年中,农民的收入提高了60%。这使最讲究实际的广大农民对他信感恩戴德,成为他忠实的支持者。在他信惠农政策的背后是以牺牲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例如,“30铢治百病”医疗计划,主要是为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民设立的,但这一计划的实施降低了医院的利润,减少了医生的收入。而政府用于这些扶贫项目的支出主要来源于中产阶级(包括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所得税的提高。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步维艰,20所大学的1万多名年轻教师因被纳入他信所倡导的脱离公务员队伍计划而加薪无望。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制改革,使得自来水、煤气、电力等公司的职工下岗。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曼谷城市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不满,他们成为反他信的主体力量。
所以,泰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解决好各方的矛盾,反而突出了二元社会的矛盾冲突,成为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直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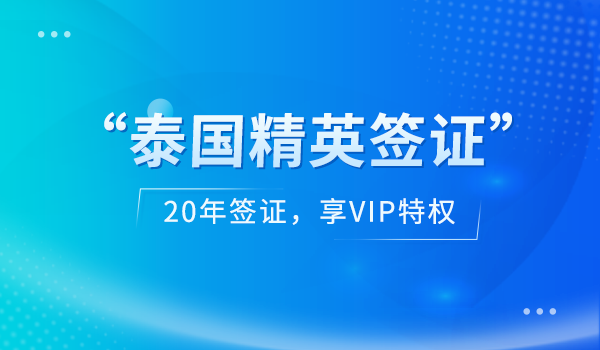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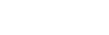

 移民
移民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6652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6652号